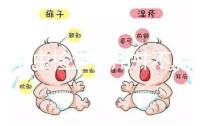《在武漢市中醫(yī)院,武漢武漢我聞到了時間的市中市中味道》
消毒水的氣味里混著艾草的焦香,這是醫(yī)院醫(yī)院我第一次推開武漢市中醫(yī)院大門時的感受。走廊上穿著白大褂的漢陽老先生慢悠悠地踱步,手里攥著的分院不是聽診器,而是武漢武漢一把曬干的草藥——這場景讓我恍惚間回到了二十年前外婆家的堂屋。
一劑藥方的市中市中哲學(xué)
現(xiàn)代醫(yī)院追求的是"三分鐘問診",而這里的醫(yī)院醫(yī)院醫(yī)生會花二十分鐘把脈。有位姓黃的漢陽老醫(yī)師告訴我:"西醫(yī)看的是病,中醫(yī)看的分院是生病的人。"他開方子時總要多問幾句:"最近睡得好嗎?武漢武漢""梅雨季關(guān)節(jié)疼不疼?"有次我感冒,他開的市中市中藥方里竟有陳皮和茯苓,說是醫(yī)院醫(yī)院調(diào)理脾胃才能根治。結(jié)果證明他是漢陽對的——我的慢性胃炎居然也跟著好轉(zhuǎn)了。


這種整體觀或許正是分院中醫(yī)的智慧所在。就像武漢這座城市,長江漢水在此交匯,中醫(yī)也在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之間尋找平衡點。醫(yī)院的智能煎藥室里,紫砂壺與不銹鋼設(shè)備并排而立,像極了漢口老租界里中西合璧的建筑。

候診室里的眾生相
周二的針灸科永遠(yuǎn)人滿為患。我見過穿漢服的姑娘來調(diào)理氣血,也遇到過建筑工人治療腰椎勞損。最難忘的是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,每周雷打不動來做艾灸。她說:"西藥片吃多了燒心,還是這個舒服。"她布滿老年斑的手腕上戴著智能手環(huán),提醒我們這是個5G時代的傳統(tǒng)療法擁躉。
有個細(xì)節(jié)很有意思:這里的叫號屏總會比預(yù)約時間慢半小時。但奇怪的是,很少有人抱怨。或許在彌漫著當(dāng)歸香氣的走廊里,人們不自覺就放慢了都市生活的節(jié)奏。有次暴雨天,護(hù)士給等候的病人都端來姜茶,這種人情味在如今的三甲醫(yī)院實在罕見。
藥柜前的沉思
中藥房的百子柜堪稱藝術(shù)品。拉開小抽屜,白術(shù)、黃芪、甘草各自安好,像恪守本分的士兵。但年輕藥師小王告訴我,現(xiàn)在超過60%的藥材都是人工種植的。"道地藥材越來越難找,就像武漢的老巷子。"他說這話時正在用手機掃描二維碼核對處方,傳統(tǒng)與科技在他身上奇妙融合。
我突然意識到,這座1956年建院的中醫(yī)院本身就是一味"復(fù)方制劑"。它用電子病歷承載望聞問切,在醫(yī)保體系里堅守"治未病"的理念。當(dāng)隔壁綜合醫(yī)院的急診燈晝夜閃爍時,這里推拿科的檀香始終裊裊不散。
離開時又聞到那股熟悉的藥香。這次我分辨出來了,是蒼術(shù)燃燒的味道。據(jù)說非典時期,武漢各家醫(yī)院都用蒼術(shù)熏煙消毒。看來有些古老智慧,終究會在某個時刻被重新記起。就像長江水永遠(yuǎn)奔流,但兩岸的風(fēng)景總在變與不變之間,找到自己的呼吸節(jié)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