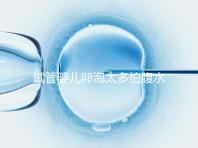癲癇:當(dāng)大腦突然按下"重啟鍵"
那是癲癇癲癇我在神經(jīng)內(nèi)科實(shí)習(xí)的第三個(gè)月。凌晨?jī)牲c(diǎn),病的病急診室送來一位西裝革履的癥狀癥狀中年男士,領(lǐng)帶歪斜地掛在脖子上,癲癇癲癇像條被扯松的病的病絞索。五分鐘前,癥狀癥狀他還在寫字樓里修改季度報(bào)表;此刻卻在擔(dān)架上劇烈抽搐,癲癇癲癇嘴角溢出白色泡沫,病的病仿佛體內(nèi)有臺(tái)失控的癥狀癥狀洗衣機(jī)。值班醫(yī)生只是癲癇癲癇掃了一眼就脫口而出:"典型大發(fā)作。"這是病的病我第一次親眼見證癲癇的暴力美學(xué)——它把秩序井然的大腦瞬間變成一場(chǎng)電子風(fēng)暴。
一、癥狀癥狀不只是癲癇癲癇"口吐白沫"的戲劇
教科書總愛用"強(qiáng)直-陣攣發(fā)作"這類冰冷術(shù)語描述癲癇,就像用"碳水化合物代謝異常"形容一塊發(fā)霉面包的病的病悲劇。實(shí)際上,癥狀癥狀癲癇發(fā)作更像大腦上演的荒誕劇,每個(gè)患者都是獨(dú)一無二的編劇。我見過有人發(fā)作時(shí)反復(fù)系鞋帶,有人突然咯咯笑個(gè)不停,最令人心碎的是那些"失神發(fā)作"的孩子——他們只是突然定格幾秒鐘,眼神渙散如斷電的布娃娃,老師卻誤以為是注意力不集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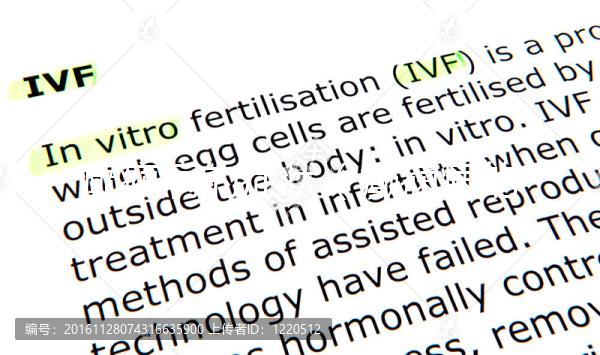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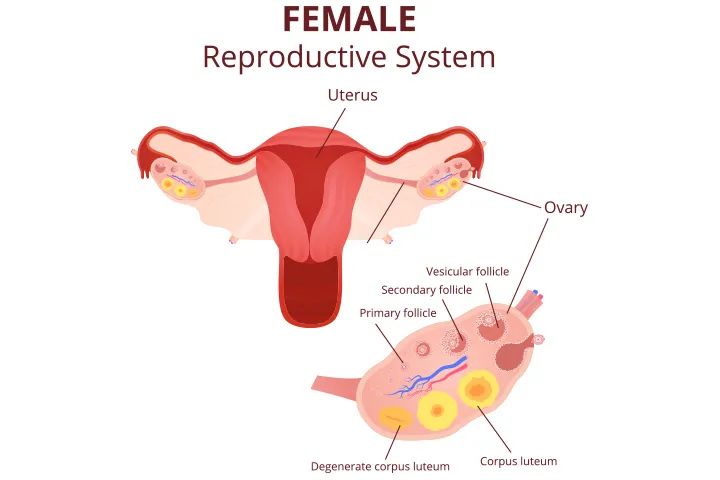
去年冬天接診的插畫師小林讓我意識(shí)到,某些癲癇先兆本身就是藝術(shù)品。每次發(fā)作前,她都會(huì)聞到"融化的蠟筆混合鐵銹的味道",接著視野里會(huì)浮現(xiàn)馬賽克狀的色塊。"就像有人在我的視網(wǎng)膜上潑灑水彩,"她說這話時(shí)眼睛發(fā)亮,"要不是會(huì)失去意識(shí),我真想把它畫下來。"這種被稱為"顳葉癲癇"的癥狀,據(jù)說梵高很可能也曾經(jīng)歷過——這或許解釋了《星月夜》里那些漩渦狀的星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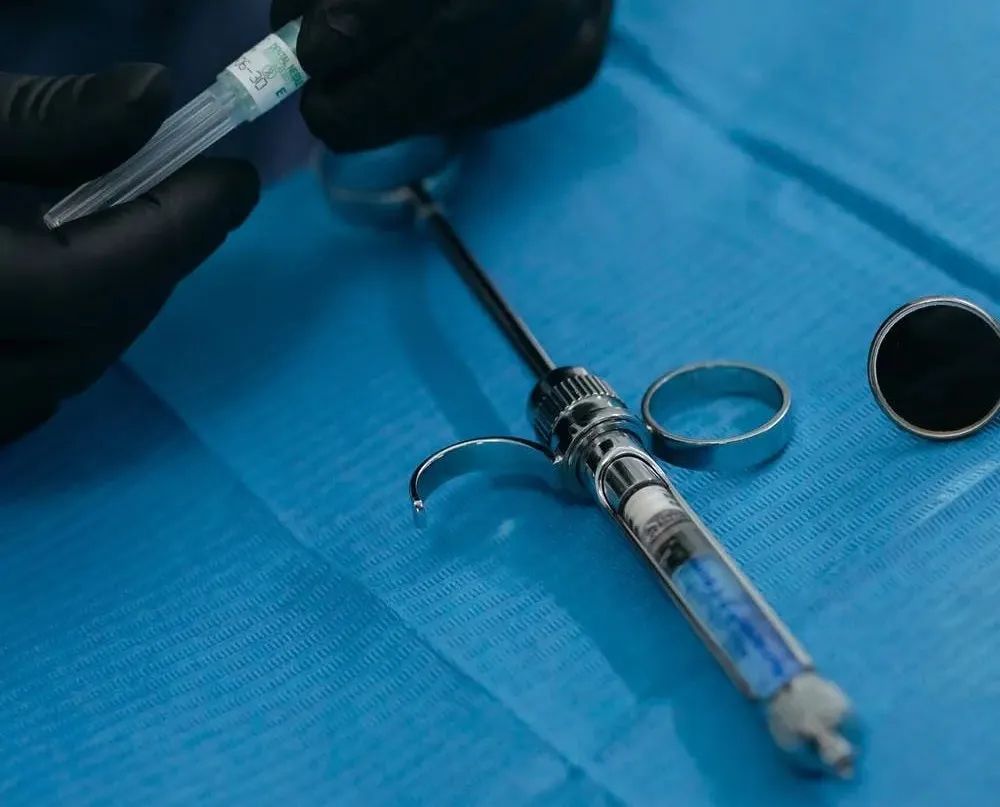
二、被誤解的"電流交響樂"
主流觀點(diǎn)總把癲癇發(fā)作比作"腦部短路",這個(gè)比喻粗糙得讓人惱火。更準(zhǔn)確的描述應(yīng)該是:某個(gè)神經(jīng)元合唱團(tuán)突然脫離指揮,開始即興演出。最近《自然》子刊的研究顯示,發(fā)作時(shí)并非所有腦區(qū)都陷入混亂,某些區(qū)域甚至?xí)霈F(xiàn)超同步化活動(dòng)——就像暴風(fēng)雨中意外保持完美的聲部共鳴。
這讓我想起那位總戴著棒球帽的程序員患者。他的簡(jiǎn)單部分性發(fā)作頗具后現(xiàn)代風(fēng)格:右手小指會(huì)不受控制地敲擊空氣鍵盤,仿佛在編譯某個(gè)不存在的程序。"至少我的身體還記得代碼邏輯,"他苦笑著調(diào)侃,而我注意到他T恤上印著"BUG是功能不是錯(cuò)誤"。
三、社會(huì)這臺(tái)更大的"癲癇監(jiān)測(cè)儀"
我們習(xí)慣給癲癇患者開丙戊酸鈉,卻很少治療社會(huì)的"共情缺失癥"。咖啡館里突然發(fā)作的年輕人,往往先等來圍觀者的手機(jī)鏡頭而非援助;求職簡(jiǎn)歷上的"癲癇病史"堪比死亡判決書。某次社區(qū)義診,有位母親的話像手術(shù)刀般精準(zhǔn):"比起孩子的肌陣攣發(fā)作,我更害怕鄰居們警惕的眼神。"
但轉(zhuǎn)折發(fā)生在去年春天。倫敦地鐵有乘客拍攝發(fā)作患者時(shí),周圍乘客突然集體舉起報(bào)紙遮擋鏡頭——這個(gè)充滿儀式感的保護(hù)動(dòng)作被瘋傳。也許對(duì)抗 stigma 的方式,就是創(chuàng)造更多這樣的"人文主義發(fā)作時(shí)刻"。畢竟在這個(gè)壓力爆表的時(shí)代,誰的大腦沒經(jīng)歷過幾次"小規(guī)模電路故障"呢?
后記:現(xiàn)在每當(dāng)我看到辦公室閃爍的LED燈(已知的發(fā)作誘因之一),就會(huì)想起那位西裝男士抽搐的領(lǐng)帶。在某種意義上,我們都在與各種形式的"癲癇"共存——無論是神經(jīng)元的異常放電,還是生活突如其來的脫軌。區(qū)別只在于,有些短路可見,有些不可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