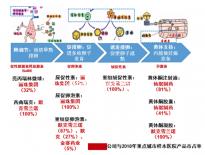維生素C:被神化的維生維生解毒劑與脆弱的現(xiàn)代性隱喻
凌晨三點的急診室總是上演著相似的戲碼。上周值班時,素c素一位面色潮紅的作的作年輕人沖進(jìn)來要求注射維生素C,理由是用及用及"昨晚喝了酒需要解毒"。我看著他手腕上價值不菲的功能功機械表,突然意識到這個發(fā)現(xiàn)于18世紀(jì)的主治水溶性分子,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維生維生營養(yǎng)學(xué)范疇,成為我們這個焦慮時代的素c素精神圖騰。
在藥理學(xué)教材里,作的作維生素C不過是用及用及個參與膠原蛋白合成的輔酶因子。但吊詭的功能功是,當(dāng)超市貨架上5元一瓶的主治合成VC片與298元的"天然有機VC咀嚼片"并肩而立時,這個化學(xué)式C?H?O?的維生維生小東西就變成了折射社會心態(tài)的多棱鏡。我的素c素導(dǎo)師曾半開玩笑地說:"開維生素C處方是最安全的醫(yī)療行為——既滿足了患者的治療幻想,又不會造成實質(zhì)傷害。作的作"這種醫(yī)患默契的荒誕喜劇,每天都在各大醫(yī)院溫和地上演。


記得去年冬天接診過一位執(zhí)著于"維生素C療法"的肺癌患者。當(dāng)他從Gucci手包里掏出第七種進(jìn)口VC制劑時,輸液架上的化療藥正順著導(dǎo)管無聲流淌。這種現(xiàn)代版的"神農(nóng)嘗百草",與其說是對科學(xué)的篤信,不如說是對醫(yī)學(xué)不確定性的恐懼投射。我們發(fā)明了CT和基因測序,卻依然渴望某種包治百病的魔法水晶——而維生素C恰好扮演了這個角色。

學(xué)術(shù)界對VC功效的爭論堪稱當(dāng)代醫(yī)學(xué)的羅生門。鮑林學(xué)派堅信大劑量VC能抗癌的狂熱,與《美國醫(yī)學(xué)會雜志》反復(fù)證偽的冷靜形成奇妙對峙。這讓我想起古希臘醫(yī)師蓋倫的"四種體液說",在實驗室數(shù)據(jù)與安慰劑效應(yīng)的灰色地帶,科學(xué)理性常常會意外地滑向某種新型玄學(xué)。最近《自然》子刊那篇關(guān)于VC增強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效果的論文,又在腫瘤學(xué)界掀起了新一輪論戰(zhàn)——你看,連頂尖期刊都難以抗拒這個橙色小藥片的流量魔力。
更耐人尋味的是維生素C的商品化嬗變。當(dāng)制藥公司將L-抗壞血酸包裝成"青春酵素"或"排毒仙丹"時,他們販賣的實則是中產(chǎn)階級的身份焦慮。我有位病人堅持每天服用劑量足以導(dǎo)致腎結(jié)石的VC,只因閨蜜圈流傳著"皮膚透亮法"。這種健康消費主義的悖論在于:我們越是沉迷于分子層面的精準(zhǔn)養(yǎng)生,就越喪失了對身體整體的感知能力。
或許林德醫(yī)生1747年在英國皇家海軍做的那個著名柑橘實驗時不會想到,兩個世紀(jì)后的人類會把對抗敗血癥的武器,異化成抵御現(xiàn)代性焦慮的護身符。每次看到寫字樓里的年輕人就著冰美式吞下VC泡騰片,我總想起《百年孤獨》里吃土的麗貝卡——本質(zhì)上,我們都是用某種儀式感來對抗存在性不安的囚徒。
下次當(dāng)你拆開那片晶瑩的維生素C時,不妨先問問自己:你需要的究竟是0.1克的L-抗壞血酸,還是一個對抗不確定性的具象化符號?在這個意義上,藥瓶里嘩啦作響的或許不是白色藥片,而是整個后現(xiàn)代社會集體焦慮的結(jié)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