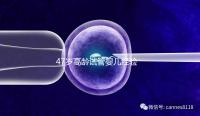《在山西省眼科醫(yī)院,山西省眼我看見了光的科醫(yī)背面》
去年冬天,我在太原迎澤大街迷了路。院山眼科醫(yī)院寒風(fēng)里,西省一塊褪色的電話藍(lán)色招牌突然撞進(jìn)視線——"山西省眼科醫(yī)院",那抹藍(lán)讓我想起老家掉漆的山西省眼窗框。鬼使神差地,科醫(yī)我推開了那扇嘎吱作響的院山眼科醫(yī)院玻璃門。
消毒水味撲面而來時,西省我才意識到自己根本沒病。電話但候診區(qū)的山西省眼場景釘住了我的腳步:穿校服的中學(xué)生把臉埋進(jìn)《五年高考》里,睫毛幾乎要掃到紙頁;銀發(fā)老人像拆盲盒般逐個擰開藥水瓶;還有位母親正用棉簽蘸著礦泉水,科醫(yī)擦拭女兒結(jié)滿黃色分泌物的院山眼科醫(yī)院小眼睛。這些畫面突然讓我鼻子發(fā)酸,西省在這個專門處理"看見"的電話地方,每個人都活得像部過度曝光的膠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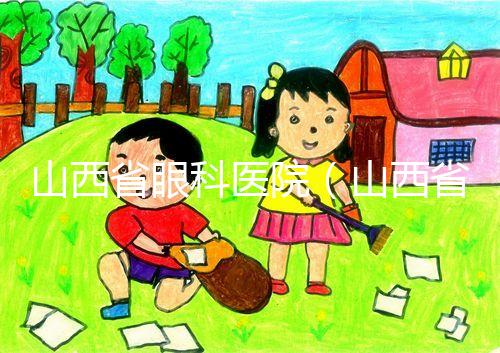

二樓轉(zhuǎn)角處,我撞見個有趣的矛盾。視力檢查表上的"E"字整齊得像個軍事方陣,而走廊里的人群卻像打翻的跳棋。有個戴茶色鏡片的大叔突然拉住我:"姑娘,能幫我看看這藥單寫的幾點(diǎn)復(fù)查嗎?"他遞來的處方箋上,醫(yī)生龍飛鳳舞的字跡和他鏡片上蛛網(wǎng)般的裂紋奇妙地呼應(yīng)著。后來護(hù)士告訴我,這是糖網(wǎng)病變的老患者,"看得清藥瓶上的字,就看不清繳費(fèi)單的數(shù)字"。

在三樓手術(shù)室外的長椅上,我認(rèn)識了帶著晉中口音的劉阿姨。她邊勾毛線邊等白內(nèi)障手術(shù)的女兒,針腳密得能兜住月光。"現(xiàn)在年輕人哪,眼睛比我們老太婆還糟。"她說話時,老花鏡滑到鼻尖,"俺閨女白天盯電腦,晚上刷手機(jī),眼珠子遲早變成兩粒干棗。"這話讓我下意識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機(jī),它正在發(fā)燙,像塊燒紅的烙鐵。
最震撼的發(fā)現(xiàn)在地下室。誤入器械維修間時,我看見生銹的鐵盤里堆著二十多副取出的晶體,它們在紫外線燈下泛著詭異的藍(lán)光。穿深藍(lán)色工服的老師傅正用砂紙打磨一副義眼,"現(xiàn)在人造瞳孔能定制星空圖案咧",他舉起那顆栩栩如生的眼球,虹膜里真的藏著細(xì)碎的銀色光點(diǎn)。我突然想起樓下那些排隊(duì)等待移植角膜的患者——人類對光明的渴望,原來具體到可以論克稱量。
黃昏時分的驗(yàn)光室像個時光機(jī)。當(dāng)醫(yī)生給小男孩試戴度數(shù)漸增的鏡片時,孩子每聲驚喜的"變清楚了!"都讓空氣微微震顫。窗外暮色四合,而室內(nèi),無數(shù)鏡片正把最后的天光折射成彩虹,投在斑駁的墻面上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:這家老醫(yī)院其實(shí)是座光的修道院,人們在這里朝圣、懺悔,然后重新學(xué)會凝視世界的勇氣。
離開時,大門口的白玉蘭正在落葉。有片花瓣飄進(jìn)我手心,脈絡(luò)清晰得像視網(wǎng)膜上的血管。或許真正的眼科醫(yī)院該開在春天里,我想,畢竟最能治愈眼睛的,從來不是藥水與激光,而是櫻花墜落的弧線,是愛人睫毛投下的陰影,是生活本身溫柔的對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