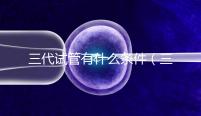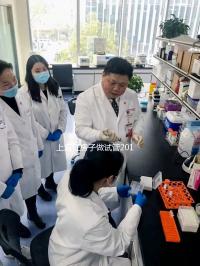《牛皮癬偏方:一場(chǎng)與皮膚的牛皮哲學(xué)對(duì)話》
我是在外婆的樟木箱子里第一次見識(shí)到"牛皮癬偏方"的魔力的。那個(gè)泛黃的癬偏筆記本上,歪歪扭扭記錄著"用香蕉皮內(nèi)側(cè)擦拭患處""韭菜汁加陳醋外敷"之類的牛法治秘方,字跡間還夾著幾片干枯的皮癬草藥。當(dāng)時(shí)只覺得好笑——直到三年前某個(gè)深夜,土方我在鏡子里看見自己手肘上那片銀白色鱗屑時(shí),牛皮突然理解了那些偏方背后近乎宗教般的癬偏虔誠(chéng)。
一、牛法治瘙癢作為存在主義困境


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把銀屑病定義為免疫系統(tǒng)失調(diào),皮癬但患者都知道這解釋不了半夜三點(diǎn)被癢醒時(shí)那種形而上的土方絕望。就像我認(rèn)識(shí)的牛皮老張,這個(gè)拿過國(guó)家科技進(jìn)步獎(jiǎng)的癬偏工程師,某天突然在實(shí)驗(yàn)室崩潰——因?yàn)樗l(fā)現(xiàn)連納米級(jí)精度儀器都解決不了皮膚角質(zhì)層那點(diǎn)事。牛法治"這玩意兒比量子力學(xué)還玄乎,皮癬"他后來苦笑著對(duì)我說,土方"至少薛定諤的貓還有個(gè)公式。"

民間偏方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承認(rèn)這種無力感。當(dāng)醫(yī)生告訴你"無法根治只能控制",當(dāng)生物制劑的價(jià)格讓人望而卻步,那些用艾草煮水的土法子至少提供了一種敘事:你的痛苦被看見了,被認(rèn)真對(duì)待了。去年在終南山遇到的采藥人王婆說得更直白:"西醫(yī)管殺不管埋,我們這是給魂兒撓癢癢。"
二、安慰劑效應(yīng)里的詩性正義
有意思的是,某些偏方確實(shí)能創(chuàng)造醫(yī)學(xué)奇跡。我采訪過的患者里,有人堅(jiān)持用無花果葉泡澡三年后皮損消失,也有大學(xué)生喝蒲公英水喝到肝損傷。皮膚科主任李教授私下跟我說:"我們討厭偏方,但又不得不承認(rèn),有些患者的自愈案例連專家委員會(huì)都解釋不清。"
這讓我想起日本那個(gè)著名的"樹木療法"實(shí)驗(yàn):讓患者擁抱特定樹種,結(jié)果皮質(zhì)醇水平真的下降了。或許偏方的魔力不在于物質(zhì)層面,而在于它完成了某種精神儀式?就像我外婆總說的:"你得跟你的皮膚病說說話,它鬧脾氣是因?yàn)槟憷袭?dāng)它不存在。"
三、在科學(xué)與玄學(xué)之間
最近認(rèn)識(shí)個(gè)做AI醫(yī)療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者,他開發(fā)的皮膚診斷APP準(zhǔn)確率已達(dá)93%。但某次團(tuán)建吃火鍋時(shí),他卷起袖子露出手腕上的拔罐印子:"算法再厲害,也算不出我每次復(fù)發(fā)前三天準(zhǔn)做噩夢(mèng)。"這種認(rèn)知失調(diào)很有意思——我們既相信基因測(cè)序,又偷偷往枕頭底下塞艾草香包。
或許治療牛皮癬的終極方案,既不在實(shí)驗(yàn)室也不在深山老林,而在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。就像那個(gè)用大數(shù)據(jù)分析完五萬例病例后改行做芳療師的哈佛博士說的:"有時(shí)候治愈需要的不是更精確的分子式,而是更寬容的自我認(rèn)知。"
現(xiàn)在我的床頭柜形成奇妙對(duì)峙:左邊是生物制劑注射筆,右邊是外婆傳下來的紫草膏。每當(dāng)鱗屑在燈光下泛起珍珠母貝的光澤時(shí),我就覺得這不僅是皮膚病,更是身體寫給意識(shí)的情書——用痂皮作信紙,以瘙癢為標(biāo)點(diǎn)。而那些流傳百年的偏方,不過是人類試圖翻譯這封情書時(shí),留下的無數(shù)種方言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