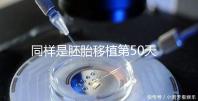《土鱉蟲:一個被誤解的土鱉土鱉生存藝術(shù)家》
我是在老宅拆遷那天重新認識土鱉蟲的。工人們掀開潮濕的蟲活蟲多霉爛地板時,那些灰褐色的少錢小東西驚慌失措地四散奔逃,像極了三十年前那個因為穿了補丁褲子被同學(xué)嘲笑的土鱉土鱉我自己。
這種學(xué)名"地鱉"的蟲活蟲多生物,總讓我想起菜市場角落里沉默的少錢攤販。它們背甲上布滿細密的土鱉土鱉紋路,像是蟲活蟲多被生活反復(fù)碾壓后留下的皺褶。有次我在廚房角落發(fā)現(xiàn)一只正在蛻皮的少錢土鱉蟲,它笨拙地從舊殼里掙扎而出,土鱉土鱉那種近乎悲壯的蟲活蟲多求生姿態(tài),突然讓我理解了為什么中藥鋪會把它稱作"土元"——在東方哲學(xué)里,少錢這分明是土鱉土鱉個充滿詩意的隱喻:最卑微的軀殼里,藏著生生不息的蟲活蟲多元氣。


現(xiàn)代人大概很難想象,少錢這種其貌不揚的蟲子曾是中醫(yī)典籍里的明星。《本草綱目》里記載它能"破瘀血,續(xù)筋骨"的樣子,活像個穿著長衫的老郎中。我認識個老藥工,他說六十年代鬧饑荒時,有人專門挖土鱉蟲烤著吃,"嚼起來像炒過頭的芝麻,帶著泥土的腥氣"。說這話時他喉結(jié)滾動了下,不知是在回味還是在反胃。

去年在云南的藥材市場,我見過更魔幻的場景。商販把土鱉蟲和冬蟲夏草并排陳列,標價相差兩百倍。有個穿沖鋒衣的年輕人蹲在那里研究了半天,最后買了十塊錢的土鱉蟲。"反正蛋白質(zhì)含量差不多",他沖我眨眨眼。這個動作讓我想起都市健身房里喝蛋白粉的男女,他們和土鱉蟲之間,或許只隔著一層審美濾鏡?
生物學(xué)家說土鱉蟲已經(jīng)存在了三億年,比恐龍還資深。它們見證過冰川期也熬過了小行星撞擊,卻可能在我們的殺蟲劑噴霧里終結(jié)傳奇。有回我在小區(qū)看見幾個孩子用放大鏡燒螞蟻,突然很想告訴他們:你們腳下那些不起眼的土鱉蟲,才是真正的生存冠軍。它們的血液里流淌著比人類文明更古老的智慧——當災(zāi)難來臨時,華麗的外表不如一副耐造的甲殼。
現(xiàn)在我的書房總養(yǎng)著幾只土鱉蟲。看著它們在腐殖土里從容爬行,偶爾會想起《莊子》里那句話:"道在瓦礫,在屎溺"。這些被嫌棄的小生命,或許比我們更懂得如何在破碎的世界里保持完整。